北京中医白癜风医学研究 http://www.paisufa.com/ 导读:李神经平台隆重推荐
摘要:
年,心血管领域在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学科发展、智能技术应用、国际合作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在高血压、心力衰竭、冠心病、降脂治疗及心律失常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指南。本文就高血压的控制目标、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冠心病的药物治疗、新型降脂药物及心律失常的器械治疗进行概述。
1,高血压
年高血压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事件是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学会(AHA)发布了新的高血压指南,彻底改变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1-3],将高血压的诊断界值定义为≥/80mmHg(1mmHg=0.kPa)。该指南认为血压/80mmHg为正常,~/80mmHg为升高,收缩压~mmHg和(或)舒张压80~89mmHg为Ⅰ期高血压,收缩压≥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为Ⅱ期高血压;并顺理成章地将降压治疗的达标值确定为/80mmHg。ACC/AHA的高血压诊断标准目前尚未得到其他学术组织的普遍认可。
在年初,美国医师协会(ACP)和美国家庭医师协会(AAFP)联合推出指南,建议60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降压目标为mmHg[4]。年中期,加拿大推出了版高血压指南[5]。该指南的特点是明确血压测量的4种场景:普通诊室血压测量,医疗机构内自动血压测量,家庭自测血压及动态血压监测。依据血压测量的场景不同,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不同。其中医疗机构内自动血压测量诊断高血压的界值为/85mmHg,而诊室非自动血压测量时高血压的诊断界值仍为/90mmHg。尽管高血压诊断界值因测量场景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降压达标的基本目标值仍为/90mmHg。
虽然ACC/AHA推荐降压治疗的目标值为/80mmHg,但对此仍颇有争议。
Weiss等[6]对21项涉及60岁及以上年龄的高血压患者的荟萃分析表明,至少要将收缩压降低到mmHg以下;但将收缩压降至mmHg以下则缺乏坚实的证据。强化降压会增加医疗花费、增加低血压及晕厥的风险,但不增加跌倒及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B?hm等[7]对ONTARGET和TRANSCEND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降压治疗后血压低于/70mmHg时,心血管复合终点事件风险增加。对于单纯收缩期高血压,VALISH试验表明,收缩压与心血管预后终点呈明显的J型曲线,最佳的收缩压界值为mmHg左右(~mmHg)[8]。CSPPT试验表明,对于没有卒中、心肌梗死、糖尿病、或肾功能减退的中国高血压患者,脑卒中风险与收缩压亦呈J型曲线关系,最佳的收缩压水平为~mmHg[9]。CSPPT是很少证明在一级预防中,脑卒中风险与收缩压呈J型曲线关系的临床试验。Bangalore等[10]对17项临床试验涉及例高血压患者(人年随访数据)进行的荟萃分析表明,降压治疗收缩压目标值mmHg是最佳的获益/安全平衡点。对没有慢性肾脏病(CKD)的患者,SPRINT研究的次级终点分析表明,强化降压会增加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但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获益远高于肾脏不良事件的不良影响[11]。荟萃分析表明,对于有症状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即使血压在正常或正常高值范围,降压治疗也可能获益[12]。
顽固性高血压仍然是临床治疗难题。顽固性高血压的确切患病率实际上并不清楚。
Sinnott等[13]对英国例应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所进行的人群研究表明,顽固性高血压患病率在年为1.75%,此后逐年升高,至年达到峰值为7.76%;此后进入平台期,在年为6.64%。这项研究提供了近年现实世界中顽固性高血压的较为可靠的患病率。Tataru等[14]对6项涉及例顽固性高血压患者RCT研究所进行的荟萃分析表明,螺内酯是最为有效的治疗药物。螺内酯可使诊室血压进一步下降10~20/3~9mmHg,使家庭自测血压下降10/4mmHg。与多沙唑嗪和比索洛尔相比,螺内酯可以更有效地降低收缩压。ROXCONTROLHTN试验表明,通过在髂动、静脉之间植入器械形成持续性髂动静脉瘘可以有效地进一步降低顽固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且其临床降压效果至少可持续1年[15]。CALM-FIM_EUR试验表明,经皮颈动脉血管内植入压力反射放大装置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可接受的安全性[16]。曾经一度低迷的经肾动脉交感神经去除术在年迎来转机。SPYRALHTN-OFFMED试验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中证明,与假手术组相比,经肾动脉交感神经去除术可以明显降低诊室血压和24小时动态血压;且降压效果至少可持续3个月[17]。SPYRALHTN-OFFMED试验给经肾动脉交感神经去除术这项技术重新带来了生机。
中国的高血压控制情况仍未有明确改善。
Li等[18]对-年间31个省18岁以上的例人群的普查表明,高血压的现患率为27.8%;在所有高血压患者中,仅31.9%是既往诊断出的;高血压的总的控制率为9.7%。Lu等[19]对中国大陆31个省计例35~75岁社区人群普查结果显示,高血压的现患率为44.7%,药物治疗率为30.1%,血压控制率为7.2%。高血压患者最常被处方的药物为钙拮抗剂(55.2%);在血压未达标的患者中,81.5%仅用了1种降压药物。基层医疗机构降压药物短缺的现象普遍存在[20]。
Bennett等[21]对42项试验涉及例高血压患者的荟萃分析表明,2种以上1/4标准剂量的降压药物联合可有效地降低血压,其效果可与单一标准剂量的降压药物疗效相似,但可以明显降低不良反应。Chow等[22]的研究表明,4种1/4标准剂量的降压药物联合可有效地降低血压。曾有假设亚洲人群可能从钙拮抗剂治疗中获益更多,但是Tran等[23]进行的荟萃研究表明,在亚洲人群中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并不比其他一线降压药物更有效地降低全因死亡、心血管不良事件、脑卒中、心力衰竭及冠状动脉血运重建风险。但是,在心血管预后方面,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也不逊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类药物。
2,心力衰竭
年,ACC/AHA对其年版心力衰竭指南进行了更新[24]。更新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对于呼吸困难的患者,检测脑钠肽(BNP)或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有助于诊断或排除心力衰竭;②入院时检测BNP/NT-proBNP或肌钙蛋白有助于判断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③出院前检测BNP/NT-proBNP有助于判断心力衰竭患者出院后的预后;④增加了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作为改善射血分数减低心力衰竭(HFrEF)患者的药物,且不推荐ARNI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类药物联合应用;⑤推荐伊伐布雷定用于心率高于70次/min的HFrEF患者;⑥对于某些合适的射血分数保存的心力衰竭(HFpEF)患者,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可能降低其再住院风险。
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在年仍然停滞不前,多个临床试验均以阴性结果告终。
LEVO-CTS试验对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35%的拟行心脏外科手术的心力衰竭患者进行了研究,共例心力衰竭患者入选。试验组于术前应用左西孟旦24小时,对照组使用安慰剂治疗。研究结果表明,术前预防性应用左西孟旦并不能改善患者住院期间及术后30天预后[25]。CHEETAH试验表明,对于围手术期接受机械辅助的心脏外科患者,左西孟旦也不能改善术后30天的预后[26]。TRUE-AHF试验表明,尽管存在有益的血流动力学效果,但新型血管扩张剂乌拉立肽并不能改善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近期和远期预后[27]。ATHENA-HF试验表明,与常规剂量的螺内酯(0~25mg/d)相比,连续96小时的高剂量螺内酯(mg/d)并不能改善急性心力衰竭30天内的预后[28]。Lim等[29]的大规模观察性研究表明,硝酸盐类药物不能够改善HFpEF患者的预后。GUIDE-IT试验表明,与常规策略相比,将LVEF减低心力衰竭患者的NT-proBNP控制在0pg/ml以下并不能改善患者的远期预后[30]。Eisen等[31]对ENGAGEAF-TIMI48试验的事后分析表明,对于不合并心力衰竭的心房颤动患者,地高辛使心原性猝死的风险增加51%;对于合并心力衰竭的心房颤动患者,地高辛明显增加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心原性猝死及由心力衰竭或心原性休克导致的死亡风险。Al-khateeb等[32]的观察性研究也表明,无论是缺血性还是非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长期应用地高辛均增加HFrEF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
心力衰竭的器械治疗仍然是改善心力衰竭长期预后的研究热点。
Narayanan等[33]对-年间6项涉及例患者的RCT试验进行的荟萃分析表明,与药物治疗相比,心脏同步化治疗(CRT)可以显著改善非缺血性HFrEF患者的长期预后;但与CRT相比,CRT/D未能显示进一步改善HFrEF患者的预后。Golwala等[34]对6项涉及例非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RCT试验所做的荟萃分析表明,单纯CRT并不能使非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而单纯植入性心脏复除颤器(ICD)或CRT/D则分别使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4%和23%。由此可见,采用何种模式的器械治疗非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尚不能确定。CAMERA-MRI试验表明,对于合并心房颤动的HFrEF患者,采用射频消融恢复窦性心律较单纯药物进行室率控制能更好地改善LVEF;特别是对那些磁共振检查无明显心肌纤维化的患者效果更好[35]。
血压是活体上反映心脏后负荷的重要指标,同时又是最重要的生命指标。但是在心力衰竭患者,最适合的血压水平仍不清楚。
韩国急性心力衰竭注册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信息[36]。该研究对例连续入选的心力衰竭患者进行中位2.2年的随访,治疗后的血压与全因死亡呈明确的J型曲线关系。心力衰竭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最合适的血压为.4/72.4mmHg,收缩压mmHg会明显增加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年ACC/AHA更新的心力衰竭指南也推荐合并高血压的心力衰竭患者(包括HFpEF和HFrEF患者)收缩压应控制在mmHg以下[24]。同样,作为最重要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心率的变化也同样重要。Vazir等[37]对TOPCAT研究的后续分析表明,对于HFpEF患者,随访中心率下降超过10次/min,全因死亡风险下降32%;心率升高超过10次/min,则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住院期间体重改变对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有明显影响。Ambrosy等[38]对ASCEND-HF试验的事后分析表明,住院期间体重降低1kg的心力衰竭患者,体重每增加1kg,30天死亡或再住院风险增加16%;出院后体重增加1kg以上的患者,其天的死亡风险亦增加16%。该研究提示体重监测在心力衰竭诊治中具有重要作用。Matsue等[39]研究发现,在急性心力衰竭患者,较高的血尿素氮/肌酐比值提示较差的临床预后。Sud等[40]的研究表明,住院时间与30天死亡或再住院呈U型关系,住院时间为5~6天的患者30天因心力衰竭或心血管原因再住院的风险最低。过长的住院时间可能反映患者病情较重,而过短的住院时间可能提示治疗不充分。Aldahl等[41]对丹麦全国注册研究中的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分析表明,血钾水平与90天的预后呈U型曲线关系。血钾低于3.5mmol/L或高于5.0mmol/L均有较高的死亡风险。进一步研究上述这些临床常用而便捷的指标对于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可能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射血分数中间值的心力衰竭(HFmrEF)是近年新提出的心力衰竭亚组人群,但其很多临床特征尚待进一步认识。
Sartipy等[42]对SwedeHF的数据分析表明,心力衰竭患者心房颤动的患病率与射血分数平行,心房颤动在HFrEF、HFmrEF及HFpEF患者中的患病率分别为65%、60%和53%。Tromp等[43]研究发现,在急性心力衰竭患者,BNP水平与LVEF呈相反趋向,其在HFrEF、HFmrEF及HFpEF患者中的水平分别为pg/ml、pg/ml及pg/ml。HFrEF患者升高的生物标志物主要为与心脏牵张有关,HFpEF患者升高的生物标志物主要与炎症有关,而HFmrEF患者升高的生物标志物则与心脏牵张和炎症均有关。Shah等[44]对GWTG-HF数据库中例心力衰竭患者随访研究表明,HFrEF、HFmrEF及HFpEF患者的5年病死率相似,分别为75.3%、75.7%和75.7%。CHART-2研究表明,HFmrHF及HFrEF转换为其他类型较常见,但HFpEF转换为其他类型的心力衰竭则相对少见。HFmrEF1年和3年转换为HFpEF的发生率为44%和45%,而转换为HFrEF的发生率则分别为16%和21%。HFmrEF患者的1年病死率与HFpEF患者相似,低于HFrEF患者;但一旦HFmrEF转换为HFrEF,其1年的病死率即会明显升高[45]。CHART-2研究提示,HFmrEF并不一定是一种独特类型的心力衰竭,而仅仅是HFrEF与HFpEF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但更接近于HFpEF。
荟萃分析表明,可溶性ST2(sST2)可以作为门诊心力衰竭患者或急性心力衰竭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预后指标[46-47],且其预后判断价值独立于NT-proBNP测定[48]。
CHAMPION试验表明,采用植入式设备监测心力衰竭患者的肺动脉压力并指导患者的治疗,可以明显改善HFrEF患者的远期预后(再住院风险下降43%,死亡风险下降57%)[49]。Desai等[50]对例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也支持CHAMPION试验的结论。
3,冠状动脉疾病
抗栓治疗过程中发生出血是临床上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何时及如何重新启用抗栓药物更是缺乏一致意见。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推出了冠心病和(或)心房颤动患者出血后重启抗栓治疗的专家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颅外出血后抗血小板药物重启、颅外出血后抗凝/抗血小板药物重启及颅内出血后抗栓药物的重启3个方面[51]。
对于颅外出血后抗血小板药物重启策略,共识推荐如下:①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或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1个月内发生出血的患者,继续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当病情稳定后尽快恢复第2联抗血小板药物。②对于ACS或植入第二代药物支架(DES)术后1~12个月发生出血的患者,建议最好在出血控制3天内恢复低剂量阿司匹林,根据对缺血/出血风险的评估决定是否加用第2联抗血小板药物;对于出血发生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3个月内且植入支架为第二代DES的患者,建议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时间为3个月;对于出血发生在PCI术后3个月以上且有再发出血风险的患者,建议仅用1联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③发生出血患者的P2Y12受体拮抗剂选择推荐首选氯吡格雷。④对于未行PCI的ACS患者,发生出血后的抗血小板治疗采用1联抗血小板药物。⑤对于所有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建议加用质子泵抑制剂(PPI);优先选用与抗血小板药物相互作用可能性较小的PPI(如泮托拉唑)。对于颅外出血后口服抗凝剂和/或抗血小板药物的重启策略,共识推荐如下:①PCI合并非瓣膜病房颤患者在应用3联抗栓治疗过程中发生出血后,仅保留1联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如果是在PCI术后1个月内则保留氯吡格雷。口服抗凝药如果是维生素K拮抗剂(VKA),则保持INR控制在2.0~2.5之间;如果是新型口服抗凝剂,则使用预防脑卒中时的最低推荐剂量。②在使用双联抗栓治疗期间发生严重出血的患者,如果已经超过1年,可以停用抗血小板药物。③ACS/PCI合并非瓣膜病房颤患者在双联或3联抗栓治疗过程中发生出血,如果脑卒中风险较低(CHA2DS2-VaSc评分男性1分、女性2分),推荐采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治疗1年。对于抗栓治疗过程中发生颅内出血患者重启抗栓治疗方面仍缺乏具体的建议。共识推荐:①对于颅内出血后何时及如何启用口服抗凝剂,需要就血栓和再发颅内出血风险与神经科医师充分沟通,制定个体化的策略。②在非机械性人工心脏瓣膜置换的患者,应首先考虑新型口服抗凝剂,并采用预防脑卒中时推荐的最低有效剂量。
新型P2Y12受体拮抗剂在临床上进一步广泛应用。临床实践中,可能遇到替格瑞洛和氯吡格雷之间的相互转换。年更新的ESC关于冠心病患者抗血小板治疗指南及多位国际专家达成的共识是:具体的转换策略取决于ACS或PCI术后时间。在ACS或PCI术后早期,需要将氯吡格雷转换为替格瑞洛时,不论氯吡格雷服用时间及剂量如何,均需给予替格瑞洛负荷量(mg);而当需要将替格瑞洛转换为氯吡格雷时,应在最后一剂替格瑞洛24小时后给予氯吡格雷负荷量mg。在ACS或PCI术后晚期,当需要将氯吡格雷转换为替格瑞洛时,应在最后一剂氯吡格雷24小时后直接给予替格瑞洛维持量(90mg,2次/d);而当需要将替格瑞洛转换为氯吡格雷时,其转换方法与在早期时的转换方法相同,即在最后一剂替格瑞洛24小时后给予氯吡格雷负荷量mg[52-53]。
TOPIC试验表明,在接受PCI且初始P2Y12受体拮抗剂为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的ACS患者,如果术后1个月内没有不良心血管事件,将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转换为氯吡格雷并不增加缺血事件风险,但会明显降低出血风险[54]。在氯吡格雷反应好的患者,在转换后获益更大[55]。TROPICAL-ACS试验表明,在接受DES治疗的ACS患者,在PCI术后1个月内即根据血小板受抑制情况将普拉格雷转换为氯吡格雷并不增加缺血性不良事件风险,但也没有降低出血事件风险[56]。Choi等[57]研究表明,即使低剂量的替格瑞洛(90mg/d)其抗血小板作用也强于标准剂量(75mg/d)的氯吡格雷;而且替格瑞洛90mg顿服的疗效优于45mg2次/d的效果。另外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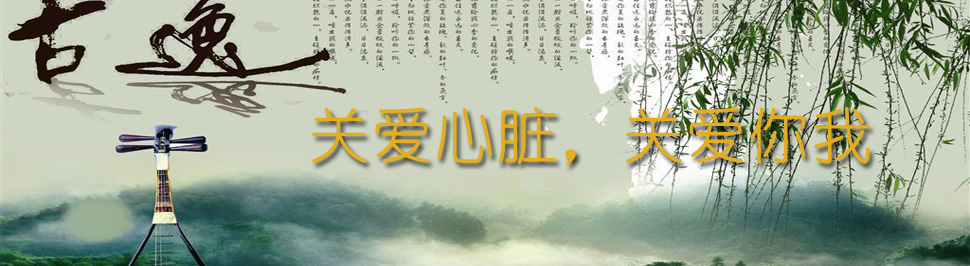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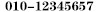 E-Mail: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