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荨麻疹医院 http://m.39.net/pf/a_9203433.html
明王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空前加强;社会经济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进一步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世界文化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明朝的地方学校教育也达到了封建社会新的发展时期。本文仅对明代地方学校的种类及功用作简要的论述。
明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明太祖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于洪武二年下令“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全国各地大建学校,出现了“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檄,山陬海涯”的可喜景象,故史称“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尤其是地方学校的建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正如《明史·选举志一》所记:“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教养之法备矣。”
有明一代,地方学校的种类繁多。不仅有政府下令兴办的府、州、县儒学,半官方性质的社学,私人兴办的义学、乡学,还有较高层次的私人讲学———书院等,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府、州、县儒学
明王朝的官办学校有两种,一为国学,二为府、州、县儒学。府、州、县学是官办儒学的初级阶段,也是普通士子们进入仕途的必由之路。明代府、州、县儒学的迅速发展与统治者的重视密切相关。
洪武二年十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府、州、县立学,他告谕中书省大臣说:“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为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选拔有实际才能,懂得经世治国之术的人充当各地的教官,而对不通事务的学究则予以罢黜,当时有教官吴从权、张恒等奉诏到京,太祖向其询问民间疾苦,二人称“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太祖因此大怒道:“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惧以无对。志圣贤之道者,故如是乎?”于是将二人流放远方。在太祖看来,教官如果不知道民间疾苦,也就不可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学生,为国家作贡献,因而他对教官的选拔要求严格。
朱元璋不仅对教官的素质要求严格,而且对其数量及待遇有明确的规定。“府学设教授一名,从九品,俸禄为米六十石,训导四人,为杂职,俸禄为二十六石。州学设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学正、教谕和训导,都是杂职,俸禄为三十六石。”
有明一代对教官的考核也有一套制度,“洪武二十六年,定学官考科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为最。举人少者为平等。至少,全无者为殿”。这使教官的升降与生员的学习好坏及中式率直接挂联,因而教官为了升迁,以科举考试为指挥棒,以督促学生准备乡试为己任,忽视了对本经、诸史的教授以及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除了对府、州、县儒学的教官要求严格外,明代对地方学校的学生也有严格的要求。据《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记载:“府、州、县学生员,责任守令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守令亲身相视,必人才挺拔,容貌端正,自年十五以上,以读《论语》、《孟子》四书者乃得预选。在内监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视,有不成才者黜退,更择人补之。”明初对府、州、县学生的入学名额也有明确的规定,“洪武十三年八月,命:在京,府学生员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县学二十人;日给禀膳,免其差徭二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要求读书的人数不断增加,为此明政府又确定了增广的人数。“两京学府增60人,在外府学增40人,州学府增30人,县学增20人。这些增广的生员出现以后,为与初设的食禀生员相区别,于是称原设生员为禀膳生员,称增广者为增广生员。其后读书人数一增再增,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生员人数的不断增加,表明地方儒学的规模不断扩大。
府、州、县学对学生的学习科目、作息时间、考核方式都有严格的要求。生员入学后,“其所业自经、史外,礼、律、书共为一科,乐、射、算共为一科,以训导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学生或教谕为之提调。经史则教授辈亲董之,自九经,四书,三书,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笺表,碑板传记之属。其考验时,观其进退揖让之节,听其语言应付之宜,背诵经史,讲明大义,问难律条,试以难决,学书不拘体格,审音以详所习之乐,观射以验巧力,稽数则第其乘除之敏钝。”由上可以看出,生员在学校所学内容比较广泛,包含经、史、律、书、数、射等,教学中也重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一般说来,府、州、县学生员的出路有三:一为取得“岁贡生员”的资格,即通过翰林院考试,进入国子学继续深造,为最终获得高官厚禄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取得“岁生贡员”的资格参加乡试,投入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以求最终取得功名。三是做乡绅。《明史》中记载:“诸生上者中式,次者禀生,年久充贡,或选拔为贡生,其累试不第,年逾五十原告退闲者,给予冠带,仍复其身。其后有纳栗,马捐监之例,则诸生又有授例而出学者矣。”
相比较而言,前两种的前途稍好一些,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既可以步入仕途,又可以光宗耀祖。入国子监读书,即使考不中举人、进士,也有机会做胥吏,其余学生回到乡间,若家境好,尚有机会通过捐纳博得一定的地位,倘若家境不好,则多流入民间,“泯然众人矣”。或教私塾,或做一些其他事情,养家糊口,有的则可能比较贫困。
(二)社学
社学设立于元代,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朱元璋出身寒微,民间情况了解较多,他知道国子监、地方府、州、县学的建立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教育要求。为了加强封建统治,教育一般的民众子弟,他对社学的发展也极为重视。“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洪武八年,朱元璋“诏有司立社学”,虽然社学的建立有利于教育普通的民众子弟,但由于许多地方官操之过急,再加上一些酷吏借机侵害平民,所以当时的社学教育并不理想。朱元璋当时对此深至愤慨,据《大诰·社学》第四十四中记载,“社学之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可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朱元璋不能容忍这种借办学鱼肉百姓,无钱不能入学的现象,因而一度下令停罢社学。但又考虑到没有社学,普通民众的教育更不可能,所以洪武十六年十月,明太祖又命复设社学,为防止官员从中渔利,同时规定“有司不得干预”,将社学的兴办交给了普通民众,这样从理论上可以避免官吏以兴办社学为名向平民敲诈勒索,但由于没有政府的有效支持,社学开始走下坡路。
社学虽是半官方的教育,但对教师的选核还是比较严格的,一般要求品德学行较高的人。朱元璋规定“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万历三年,明令社学“务求明师……其行止有亏及训诂句读韵差谬,字画不端,不通文理者,即行革退。”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社学的老师也不可能个个是名师。教师的选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官或提学官聘任。地方官员是当地的父母官,他们可以直接聘请一些人做社学的老师。如《嘉靖隆庆志》记载:成化三年(),知州李鼐建社学,“立师以专教事”,又如《庄渠遗书》中记载:魏校督学广东,亦曾令“每岁,各州县提调官以正月望后启学。先一月,具书致礼请师”。二是乡民选举,如乡民认为某人学行较高可以直接推举他做社学老师,或由乡民推举,地方官考核后,再充当社学老师。据《嘉靖龙溪县志》卷一记载“凡乡里有社学,为父兄相与议,求有学识行艺可为师表者一人,推一二有力者为纠首,以诸生姓名列于关,敬谒以请。即许可,乃岁节后卜曰备礼,延至于学。”
社学中所收的大体是儿童中较为聪颖的孩子。由于明朝统治者重视教育的目的是选拔出为明政权服务的官吏,同时教育人民遵纪守法,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不可能将所有儿童都作为教育的对象。既然科举考试严令禁止倡优隶卒参加,他们的子弟自然也就难以入学。这种限制是政府为了保证入仕队伍的纯洁性。
明代社学的招生有时存在强迫儿童入学的现象。成化年间,杨继宗为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可见,明代的社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义务教育的性质。主要还是因为统治者想通过教育向学生灌输封建思想,稳定统治,并非为了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另外,明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学,专门招收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子弟。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
社学教育内容多为《小学》、《四书》等,《嘉靖龙岩志》卷四载:近该知县汤亲课诵读之业,见得童幼所诵,皆《公理出巡录》等书,蒙养弗端,无异乎习讼成习也。已经择取教读,并令习《孝经》、《小学》,以及《四书》,经史。严行禁谕,如有乃前习读者,罪及父兄长。陈献章认为社学必须以《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小学言之,朱子《小学》书,教之之具也。……天下之事,无本不立。小学,学之本也。”明代除直接使用《小学》作教材外,还使用一些“用于历史教育、歌诗的教材以及一些综合性的训蒙教材和无专门教本的活动性教材”。
明代最高统治者很注重利用社学进行教育,朱元璋曾命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他用这种方法去鼓励民间诵习明朝的律令、《大诰》,以使百姓安分守己。弘治年间,政府下令“幼童十五以下者,送进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从小就对百姓进行封建礼仪教育。由于封建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故参加科举考试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动机,在社学接受一定的教育为以后升入儒学,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社学学生的出路不外有二:一为升入儒学,然则由于地方儒学的规模有限,再加上一些地方豪强之家的垄断,从社学升入儒学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而对广大学生,尤其是无钱无势的学生而言,返回原乡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吕坤在《社学要略》中,就明确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
(三)义学或乡学
所谓义学,就是明代史籍中时常提到的“乡馆”与“家塾”,或称“乡学”,又称“义塾”,属于私人兴办的小学。
在明初,虽然官方社学兴盛,对普及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广大农村各地情况有所不同,再加上一些大家族对社学教育不满意,因而社学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于是,地方大姓创设义塾,“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间,以为讲习之所,旁为室以供寝处”。延儒士高平为塾师,“俾里中子弟就学焉。”明中期以后,由于社学败坏,义学开始蔚成风气。据《八闽通志》中记载,富宁州每岁上元后即延师以教子弟,至八月,解馆。金华府汤溪县,乡里延师之风也极盛,据《金华府志》载:“每岁春,乡有长者,以聚众延师家塾,以训蒙童,迨冬而散”。这种延师训蒙风气的广泛存在,正是义学广泛兴起之后的一种表现。
明代的义学或乡学的形式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情况:
一是由地方官出资兴办。一些重视民间教育的地方官员为了改良民风,推行教化,利用官府的钱兴办学校,解决一些百姓子弟的教育。在福建浦城县,知府张俭也遍设义学,其教师由县观“务举保颇立行止,粗和经义,敦实持官之人。”每所学校挂上“义学”匾额,“吁令通县年十六七以下子弟赴学”。
二是由乡绅创办。由于科举中式的人可以光宗耀祖,所以一些地方大家族为了出人头地,不惜花重金聘请老师,教育本族子弟,为后来科举打基础。在吴江县,姚芳考虑到乡间中没有讲学的场所,“因即所居之近,古塘之西,创学舍一区,中为堂,翼以两厢,敝以外门……延士之贤者以主师席,凡乡间子弟自童蒙以上,悉昕来学,而免其束修”。
三是由科场失意的儒生创设。明朝中后期,随着教育的发展,参加科考的人数越来越多,科场失意者越来越多,他们常年学做八股文,不善于做其他事,故只好授徒以维持生计。这种乡馆的教学质量实在无法恭维。据明代小说《西湖二集》上记载:吃饭迟延,假说爹娘叫我做事,出贡频数,都云肚腹近日有灾。若到重阳,采两朵黄花供师母;如逢宥食,偷几个团子奉先生。
相比较而言,以上三种义学各有利弊。地方官出资兴办的学校,财政上有保证,不过一旦此官员调任他处,继任者若不重视教育,则以前的学校就会废弃。由科场失意者开办的乡学,老师较认真,不过常常为资金缺乏而苦恼。由地方乡绅创办的义学不仅资金有保障,而且对教学质量也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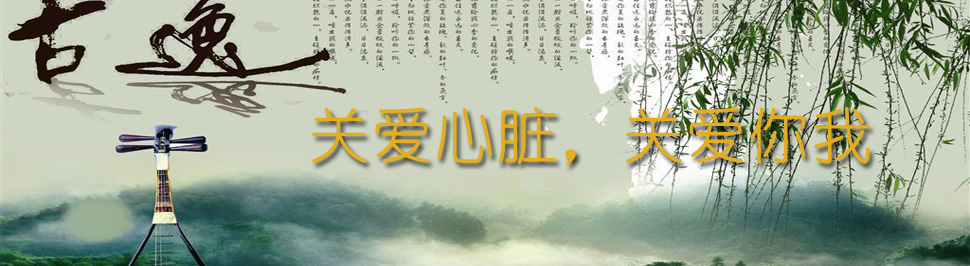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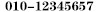 E-Mail:
E-Mail: